
回到艺术,努力攀登主题创作新高峰
文/杜学文
近年来,文艺创作表现出十分活跃的态势。首先是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出现了许多新的艺术样式。一些已有的样式也由于技术的进步在艺术表现力方面出现了新气象。如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长安三万里》等。其次是创作手法进一步丰富。在注重传统手法的同时,借鉴现代手法,特别是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使形象的立体感、厚重度得到了强化。如小说《千里江山图》《本巴》《雪山大地》等,戏剧《五星出东方》《远方的拉萨河》《右玉》等,电影《长津湖》《我们一起摇太阳》等,电视剧《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我的阿勒泰》《繁花》等,都有新的探索。再次是艺术的想象力得到强化。由繁而简,由简而繁,虚实相间,内外相融,强调表达现实精神的“非现实”性,注重想象力对作品结构与表达的意义,表现出中国文艺的新境界。
在众多的作品当中,有一类可归之为“主题创作”,就是在题材选择当中有意或无意地与当下社会关注的重要现象紧密结合起来,具有比较突出的现实意味。如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创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作、生态文明建设的创作,以及重点工程、重大事件的创作等等。这一类作品的数量比较大,参与者比较多,是中国文艺发展进步的重要方阵,表现出强烈的现实精神与艺术责任感。但是,也存在若干需要改进的问题。大致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回归于艺术。
一般来说,这类作品与现实联系比较密切,容易获得地方机构的重视。但是一些决策者也好,创作者也好,往往拘泥于具体表现本地的某一工作成效,或者宣传本地的某种文化特色,意识不到文艺创作的特殊性,习惯于从本地工作成效出发,强调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事件、真实的过程,忽略或漠视艺术创作需要的虚构、想象、典型化、抒情化,把艺术创作等同于新闻报道、工作总结,弱化或损害了作品的感染力。
就创作者而言,也存在着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片面强调“艺术性”,忽略或漠视有关题材最具现实意义与文化品格的内容;在艺术虚构上与现实生活距离过远,把真实的事情表现得不可信、不真实;在表现手法上看似创新却落入窠臼,注重外在附属形态的使用,如繁杂的舞美、技术至上,不注重内在精神世界的揭示。一些艺术家对别人的意见、建议呈抵触之态,不能正确地考虑、吸纳。这些看似“艺术”的行为恰恰违背了艺术的本质,走向了另一种片面。
主题创作在现实中有很多成功的范例。如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表现大革命时期上海地下党建立代号为“千里江山图”的交通线,以掩护中央机关的战略转移。按照一般的写法,应该是交代清楚任务,强调其重要性,以及完成转移的光荣感。但作者却另辟蹊径,“异想天开”,设计了一个“不知道”的结构模式——不知道谁是参与这一工作的同志,不知道谁是这项工作的负责人,不知道要转移谁,也不知道要转移到什么地方,如何转移。这么多的“不知道”虽然也符合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但对叙述而言却是巨大的挑战——正是在这诸多的“不知道”中小说显得扑朔迷离,表现出更多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应该说,《千里江山图》在小说的结构与叙事方面有突出的创新,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的表现手法。也正是由此提升了中国小说的艺术品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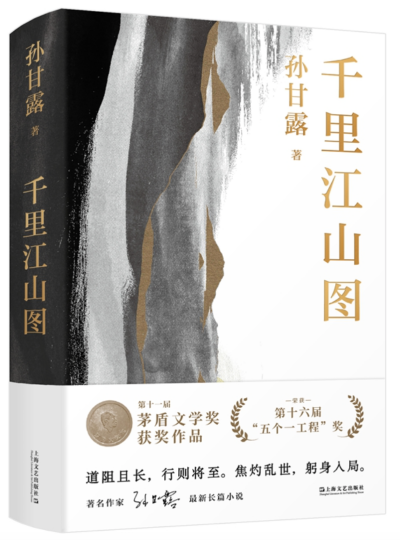
孙甘露著《千里江山图》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创作是从现实中的概念出发,还是从生活中的形象出发?这对主题创作而言是极为关键的。文艺创作肯定不能脱离现实,应该有现实精神、现实意义。但在表现现实的时候,是表现现实中抽象的概念还是塑造现实中生动的形象?这是完全不同的。从概念出发就要证明并得出明确的结论。其思维方式是以逻辑论证为主的。作者将努力罗列事实以证明概念的正确性。而从形象出发则是以刻画人物为出发点。其思维方式是以情感感悟为主的。作者将通过描写人物的性格与细节、心理,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情感状态来触动欣赏者,让欣赏者在人物具体的、富有个性意义的行为中接受某种价值的影响。这种表现很可能并没有直接点明结论,却会使欣赏者领悟其中的价值选择。这二者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
从形象出发,最重要的是要从人物的性格出发,以塑造出个性鲜明、活色生香的典型形象。
在很多情况下,为了赶节点,完成任务,创作者虽然也做了点采风的工作,但基本上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没有深入的体验。有的连基本情况都没有弄清楚,更不用说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现实状态、民俗风情、人物个性的体察了。这自然就是隔着靴子挠痒痒,抓不到痒处,是一种似是而非、知而不察的了解。写脱贫攻坚,却不知道第一书记是什么意思,什么职责;写地下工作,却不了解地下工作者的生活细节;写重点工程,却不知道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不知道其中的技术细节。事情说完了,仿佛听了一场语焉不详的报告。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文艺创作并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达,同时也是一种“学识”表达。这种所谓的“学识”就是要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对描写对象的“认知”——把“学”转化为“识”,并进行形象性的描写,完成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思想呈现。如果《红楼梦》没有描写贾府中人怎么吃饭,怎么过节,怎么看病,怎么交往,《红楼梦》也就不存在了。套用鲁迅先生的说法,在《红楼梦》里,医生可以知道看病的药方,厨师可以知道做菜的菜单,民俗家能够发现民情,而社会活动家会在书中研究出当时的人伦现象与社会演变。正是这些看似与“主题”关系不大的东西使作品的文化品格得到了提升,亦使作品的吸引力得到了增强。而作品中的价值倾向也在这样的描写中不知不觉地表现了出来。所以,要写好作品必须深入地了解与“主题”相关的林林总总——大到历史背景、政策决策,小到衣着饮食、举手投足,都要烂熟于心,了如指掌,才能运用自如,恰到好处。
(本文经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授权发布。本文原载于《中国艺术报》2025年4月16日第5版,有删减。)

杜学文,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
作者:杜学文
编辑:施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