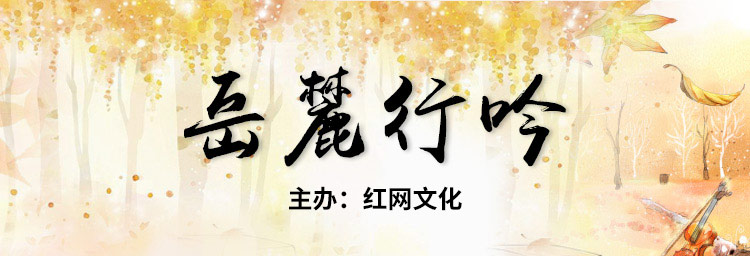

音乐剧《人间失格》演出剧照。
在世界的荒谬与生活的悲情中寻找生命价值
——音乐剧《人间失格》刍议
文/常瑞芳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哲学,给予人以灵魂的启迪。
读过《人间失格》小说或电影的人感叹:在荒谬的世界与悲情的生活中寻求温暖,在不期而遇的打击与身心的伤痛中寻找生活意义,在孤独与寂寞中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2025年3月28、29日晚,音乐剧《人间失格》在梅溪湖国际大剧院再度上演。因为该剧创造性地采用双男主交替同构演出,我便接连两天观看了该剧,这在我的观剧历史上,是不可多见的。
由染空间出品的音乐剧《人间失格》于舞台上诠释了家族与爱、环境与成长、经历与个性,以及人生自我反观与灵魂的自我救赎等艺术形而上的价值体现,以感性形式实现了哲学的抽象表达。至今为止,是我看过的最好的音乐剧,编剧从人性方面精雕细琢人物的内心世界,无论是语言的精辟、剧情的波澜起伏,还是演员的角色演绎、音乐旋律、舞美灯光,都给我强烈的震撼与艺术享受。据闻,该剧至今已经演出200多场,再度开启全国巡演仍是一票难求,场场爆满。
颠覆性的改编,双男主的戏剧性建构
“所谓世间,不就是你吗?”这部带着强烈主观意识的音乐剧《人间失格》,改编于日本小说家太宰治半自传体形式创作的同名中篇小说,编剧虽然以小说的框架为蓝本,却又脱离小说《人间失格》的藩篱,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同时,将作家太宰治和小说主人公大庭叶藏两个人建构在同一个舞台之上,以大庭叶藏虚拟人物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同时把太宰治个人情绪的宣泄和文学创作思维理念,以及他平生所创作的作品蜻蜓点水般揉进舞台剧中,展现了人性之丑陋、利己与渴望温情的复杂性,剧中人物灵魂与人格的撕裂及自我救赎等细致化表现,使该剧主题深化,直抵观众心灵。
相较于小说中封闭的自我叙事角度来展现主人公的内心挣扎、痛苦和迷茫,音乐剧通过“作家太宰治”与“虚构角色大庭叶藏”的镜像对话,将创作主体与文学客体置于同一时空维度来演绎,增强了剧目的独特性和观赏性(其双主角的交替同台演出,或许更多的考量在于青年歌手白举纲的明星效应)。如若说该剧是以大庭叶藏为主角的话,不如更贴切地说是以太宰治为视角的重头戏。太宰治是大庭叶藏的创造者,大庭叶藏为小说中的主人公,虽聚焦于具体的个人体验即非理性情绪体验为核心,但二者互为镜像,彼此灵魂浸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通又各有分别,以二维度虚实交错的时空交织,诠释存在主义与人性困境,深度剖析自我存在之状态。故而,该音乐剧通过双主角行事,即不违和,又在某种程度上演绎了人性的多样性,在文学与戏剧舞台上皆为独创;即符合当下多重构建的时尚元素,也更好地运用了多维度的形式体现内容的哲学隐喻。
这部作品最颠覆性的改编,在于为原著注入戏剧性救赎的可能。以太宰治之手创作的大庭叶藏,自述经历,到太宰治和大庭叶藏跨越时空的对话,这种创作者与造物之间的博弈关系,在交响乐渐强的推进中,升华为对艺术本质的叩问。当太宰治穿越时空与大庭叶藏共饮最后的清酒,作者与自己所创作的人物达成和解,此时,舞台上飘舞着樱花,太宰治抢过角色手中的毒药一饮而尽,慢慢走向鲜花的后台,身影消失在世间,大庭叶藏仍留在舞台,舞台上空是叠加的书,皆为太宰治平生所创作的作品,隐喻文字既是救赎的阶梯。这个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结局,让创作者以自我毁灭完成对虚构角色的赦免。
太宰治用他作品中的人物存活于世,编导用舞台语言隐喻“精神永存”的哲学思辨。
双主角的双重体验,角色与歌者的镜像共生
演员是通过生活化的表演在舞台上再现生活。化解自我,融入角色,才是好演员。
音乐剧《人间失格》时长近3小时,分为上下两场戏。该剧颇具创造性的双主角更替的同台演出,白举纲和刘令飞两位主演都是非常不错的音乐剧演员,曾经风靡全国《快乐男声》季军出道的青年歌手白举纲,其演唱音色自然是非常好的,而演员刘令飞也有着金属般的嗓音,两相比较,在对话或独白时,刘令飞的吐词与人物内心的节奏把握要胜筹一分;而从两人的身体外形上来说,白举纲似乎更接近大庭叶藏的角色扮演。
梅溪湖剧院的第一场演出,白举纲饰演剧中的太宰治,这个人物他也演得尚好。首先出场的是作家太宰治,扮演者白举纲的出场很有气度:舞台正中上方高悬着一张严肃的男性白色面具,两侧是重叠零乱白色的纸张,面具的下方以一本书的倾斜度为旋转舞台,作家太宰治从舞台后方的书边沿伸出他的手,金属般的磁音唱响剧院:“夜空闪烁,人影交错,潮起潮落,剩下孤独与我……”刘令飞饰演的大庭叶藏站在一个巨型的手掌上出场,太宰治以创作者身份与大庭叶藏展开对唱和合唱,该剧的导演和舞美设计师将故事背景的铺陈与隐喻,以无比震撼的艺术样式呈现给观众,对追求视听震撼的观众,它无疑提供了一场独特的感官盛宴。
上半场戏份主要以大庭叶藏为重头戏,太宰治偶尔穿插出场。因为我仅熟知歌手白举纲,对他的关注度自然要高一些,虽然读过小说《人间失格》,但对其改编的剧情并不完全了解。白举纲从头到脚的黑色披风礼帽加持的造型与剧中其他人物角色服饰重叠,在他将被引入秘密聚会的场域,一群同款服装造型的人物,尤其是在酒吧高台上那个后置的人物,从身材上一时难以分辨,让我产生严重的质疑,这是太宰治吗?身材与装扮上似乎是,气质上却又不像(从剧情判断当然不是,只是社团核心人物罢了),甚至于后来太宰治骑在旋转木马上出现时,再度让我猜测和质疑。
大庭叶藏遭遇友情爱情的双重背叛时,那段近乎崩溃的大段独唱,是上半场的高潮戏部分,刘令飞饰演叶藏,孤伶伶地在痛苦演唱,空旷的舞台上,给予观众的感觉有些单薄。我甚至想,或许太宰治和大庭叶藏在此时一实一虚同时出现在舞台,共同演绎,用音乐和肢体语言渲染对自我认同的迷茫,让太宰治与叶藏在不同的时空交错中,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互为镜像对话,会更有戏剧的张力,也会让观众更能体会剧中人物内心的撕裂与痛苦。尤其是下半场编剧的笔锋一转,将太宰治本体的主观意识,他对文学的追求,于独特的文学创作理念思潮阐述埋下伏笔,为后续情节二者的个性差异与和解,以太宰治为主场展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与感悟的戏份完美融合,前后呼应,自然而流畅,而不突兀。
3月29日晚,白举纲饰演大庭叶藏,上半场戏份在音乐唱词的演绎中情绪饱满。当大庭叶藏从镜面舞台深处爬出,带着被撕碎的西装与染血的衬衫唱响《人间标本》时,这位从选秀舞台走出的音乐人,将自己重塑为太宰治笔下那个“边缘生存者”,用声音与形体的双重解构,完成了一次惊人的艺术献祭。尤其是音乐场域于舞台中央的镜面装置折射出千万个破碎的大庭叶藏,当他跪伏在地唱出“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的瞬间,太宰治文字中蚀骨的那种虚无感,化作音浪冲击着观众的灵魂。
下半场戏中最颠覆认知的是对“恶”的重新诠释。当大庭叶藏用戏谑口吻唱起《作恶者的摇篮曲》,舞台突然降下无数悬浮的枕头,温柔包裹住这个“罪人”。这幕超现实场景让我惊觉:我们何尝不是用道德羽绒包裹着自己的卑劣?当祝子遭遇暴行后,她跪坐在光柱中反复呢喃“我脏了”,大庭叶藏在另一区域,用地上洁白的雪,用力地擦洗着自己身体的动作,将对自我厌恶与悔恨的复杂情绪演绎到一种极致境地,其舞台情绪饱满,给观众强烈的艺术震撼,于全场死寂中某个角落突然传来压抑的呜咽——那种集体负罪感带来的窒息,仿佛在问,这个摇摇欲坠的世界里,谁不是踮着脚尖在生存?
在音乐剧《人间失格》中,双主角的双重体验,不仅体现在他们各自对世界的理解与感悟上,更体现在他们相互之间的映照与影响上。太宰治作为创作者,他的情感与思想,通过大庭叶藏这一虚构角色得以展现,而叶藏的经历与遭遇,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太宰治内心的挣扎与痛苦。这种相互映照与影响,使得剧中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也让观众在观赏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与深刻。
《人间失格》的音乐剧场域中,音乐旋律将文字炼成直击心脏的箭矢,当白举纲饰演的叶藏蜷缩在旋转舞台上唱出《生如尘埃》,副歌部分金属质感的强混声如同玻璃碎裂,将叶藏灵魂的裂缝具象化为声波暴力;他与恒子对唱的《飞蛾与火焰》,声腔切换为气若游丝的弱声,每个颤音都像是烛火将熄前的最后抽搐。
音乐是人类情感温度的调色板,当旋律响起直抵灵魂深处,文学母题在音符碰撞中迸发出新的解读:或许真正的救赎不在于摆脱痛苦,而在于承认绝望本身即是存在的证明。
白举纲与刘令飞两位主演,以他们精湛的演技与动人的歌声,将太宰治与大庭叶藏这两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他们不仅准确地把握住了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与情感变化,更通过细腻的表演与深情的演唱,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剧中人物的世界之中,与他们一同经历那些痛苦与挣扎、欢乐与希望。两位主演的精彩演绎,无疑为音乐剧《人间失格》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震撼的舞台效果,直抵心灵的多重隐喻表达
舞台设计是空间的诗意解构,是最直观审美元素表达。
音乐剧《人间失格》舞台设计由英国著名舞美设计大师莱斯利·特拉弗斯(Leslie Travers)担纲,他以其标志性的巨型装置为该剧增添了别样的风采,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极简风格的舞台上,动态与静态装置相互映衬,灯光、音乐、舞台装置等元素相互配合,如同电影中的镜头切换,分割出不同环境空间,加之配乐烘托与场景布置,使整个舞台呈现出一种流动的画面感。旋转木马舞台、移动台阶、转盘、传送带等动态装置,营造出时光荏苒的动感和一种动荡不安的氛围,象征着角色内心的起伏。
不可否认,整个剧目舞台调度充满存在主义隐喻。旋转的斜坡舞台,既是大庭叶藏不断下坠的人生轨迹,也是太宰治笔下“倾斜的”昭和时代缩影。在《蝼蚁之歌》段落,群演们戴着面具排列成扭曲的钟表造型,在机械舞步中展现社会规训对人性的异化。当大庭叶藏与恒子在镰仓海岸相拥时,从天而降的钢丝将二人吊起,在失重状态下完成的二重唱《飞蛾与火焰》,用身体语言诠释着毁灭与救赎的辩证关系。
该剧充分运用艺术的写意、象征、隐喻等作用,如浮于空中的巨大白色人像,无言地诉说着权威与专制;舞台中一双巨手包裹着人物,即象征着孕育、创造,同时以抽象现代的美学形式,深刻诠释了太宰治和叶藏被命运掌控的无奈,寓意着社会与命运对人的束缚。而片片纸张等静态装置,则随着故事的进程不断变化、位移,有时是书,有时是屏障,又有时组成堡垒,禁锢人的心灵,如祝子被强暴后,对话大庭叶藏的质问,揭露他的懦弱、虚伪、无情、自私,祝子情绪崩溃的坐在地上悲泣,半空中,三面由片片纸张组成的白色围墙下,“唰”的一声,三面皆落下黑色帷幔,像极了一座囚牢,加上天空飘飞的雪花,这种细腻极致化的表呈,极具视觉冲击力,寓意深刻,将观众带进了强烈的戏剧情境中,引发情感共鸣。
服装造型与群舞也是紧扣剧情。懦弱而孤单的大庭叶藏被女仆猥亵,伴舞的女子紧身衣物外罩着错乱交织的黑色丝网蓬裙,隐喻罪恶、惊悚、丑陋之行为;还有随剧情戴面具或造型各不同异步舞者;更惊人的是《虚构人生》那段癫狂的踢踏舞,演员们足尖叩击地板的节奏逐渐与观众心跳共振,仿佛整个剧场都成了太宰治笔下的精神牢笼。同时,导演巧妙地运用了“镜像”这一艺术形式。通过舞台布局、灯光与音乐的巧妙配合,当大庭叶藏在崩溃的边缘挣扎时,太宰治则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地审视这一切,他的存在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叶藏内心深处的孤独与绝望。这种角色与歌者的镜像共生,不仅增强了剧目的艺术表现力,也让观众在观赏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人性的多层性,更能体会剧中人物内心的撕裂与痛苦。
其实,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样子就是自我生命的状态。无论是太宰治还是大庭叶藏,在舞台上,他们都是虚拟的艺术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一个生命都可以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模式,为人物生命自我建构什么底色,便拥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故事框架就能围绕着中心思想展开,真实的或虚拟的,都是创作者主观意思的表现。这种将文学厚度转化为剧场张力的能力,让该剧超越了简单的名著改编,创造性地构建起一个用音乐对话的现代寓言,成为具有独立美学价值的当代剧场范本。
太宰治与大庭叶藏给予我的共情是:拥有内求自省创作能力的生命力量是无限的,思想的精髓超越时空而永恒存在,但外求的生命如同暗物质,永远都是空洞状态。
从剧场出来,我的情绪仍纠结于现在时与过去时的被撕裂的痛苦与挣扎中,为了忘却,想到此悟,在春天乍暖还寒的夜晚,亦哂然一笑。
来源:红网
作者:常瑞芳
编辑:施文
本文为娱乐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